被问过一个问题:如果荒岛生活只能带一部电影,你会带上哪一部?
险些不假思虑,我脱口而出的是,雅克·塔蒂的《我的舅舅》。
在一个百无聊赖又要面对危急感的时候,还是看看笑剧更能缓解焦虑吧?
更何况,这是一部真正优雅到骨子里的笑剧,它无需利用任何一帧夸年夜的画面胳肢我们。于洛师长西席,这个貌似无业的城市中年人,彷佛存心跟“奇迹”“成功”为难刁难似的,从容地、不慌不忙地活在自己的光阴中——与孩子们玩耍、招猫逗狗、逛菜市场,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平民的乐趣,而这乐趣中蕴含着真正的优雅态度,包括彬彬有礼的风姿,乃至有人对他无礼,他也从未被激怒。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当代的”“高真个”,却焦虑满满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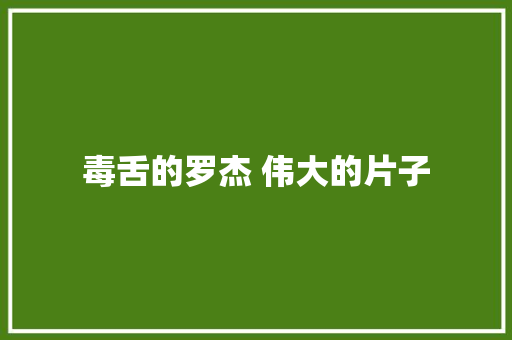
以是,就像工蜂被蜜源吸引,当看到用这部电影的剧照做封面的图书时,我不假思虑地下了单:穿着棕色翻毛皮鞋、彩条袜子、露出脚踝的裤子、半旧的巴尔肯风衣、叼着烟斗的于洛师长西席骑着自行车,后座上是嬉笑的小外甥杰拉尔——再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影响了好几代美国影迷的大影评家——罗杰·伊伯特。
好的秘密+坏的秘密
恐怕也只有这样的作者,当他利用《伟大的电影》(The Great Movies)这样的书名时,我们不会认为浮夸、噱头、危言耸听,由于他的电影评论,是真正的“为所有人”——短小精悍,又深入浅出,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支撑”,却在轻松戏谑间就精确隧道出了一部电影的秘密——好的秘密和坏的秘密。
也只有他,才绝不在意地利用“movie”这个词,用在塔尔科夫斯基、小津安二郎和伯格曼身上他同样泰然自若,而很多学者则方向于用“cinema”这个词去描述电影神殿大师们的作品。
正由于罗杰能将他们等量齐观,以是这本文集才更具有可看性,并且远远超出“佳片指南”的意义。等量齐观,绝非意味着把他拉高或把他拉底,而是适可而止。由于“伟大”也是因人而异(对付很多人来说,《龙猫》《金刚》《007 之金手指》便是“伟大”的电影),但是罗杰的评价又是中肯的,常常说出别人看不到的秘密。
例如他对《龙猫》的评价:“电影有几分悲哀,有几分恐怖,有几分惊喜,还有几分深省,正犹如生活本身。它的阐述紧扣情境而不是依赖桥段,并且见告我们,生命的美妙和想象力的源泉可以供应我们渴望的统统奇遇。”
再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罗杰的好评无疑对付这部影片以及张艺谋本人在北美的荣誉大有帮助,而对付侯麦这样的殿堂级的人物,他又如是评价:“侯麦的电影中充满了对爱的信念——或者,如果不是爱,那便是对的人由于对的情由找到彼此。他的电影中时有悲哀,但并不消沉。他的角色如此聪明,不会对失落望感到惊异。他们对生活如此兴趣盎然,因此不会沉溺于消沉的感情。他的影片之以是成功并非由于他们讲了精确的大道理,而是由于那些小小的真理。进入他的影片,便是去和那些我们乐意去结识的人为伴,然后逐渐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便是我们自己。”
大学教授+电视明星
或许也只有美国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文化氛围内才能产生像罗杰这样的影评人——他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电视明星,他以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用诙谐锐利的办法见告大众什么是好电影(当然有好坏之分),为此他不惜“毒舌”——由于好莱坞电影中有太多滥俗的内容,过量服用会生病的。他的这些“毒舌”有一部分被收入在《我知道你们又来这一套》中。不过,毒舌二字或许会导致误解。他的“毒舌”并不进行人身攻击,而是有着真正的知识人的诙谐感。试举几例:
“丑女大变身”定律:电影中涌现的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如果她梳着毫无魅力的发型,还戴着又大又厚的眼镜,那么她十有八九便是隐蔽的女主角。很快,她就会神奇地开始大变装,不仅洗手不干成完美女性,还拥有整整一个衣橱的性感衣饰;
一招变装定律:每当一个杀手要进入布满安保职员的医院暗杀一个病人时,他总是会“因时制宜”地变装成这个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医护职员,如入无人之境,当然,永久不会有人把稳到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被打断的吻:每当男女主角的嘴唇只差半厘米的时候,就一定会被打断。
实在我们不难觉察,罗杰所“毒舌”的,正是我们习气于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如此”的部分,而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工业流水线式的不雅观影习气导致了我们无法认识真正“伟大”的电影——电影除了复制、粘贴、让我们认同于生活的庸常,更可以刺破这种庸常,创造看待光阴的另一种可能的办法,从而得到深深的启迪,由于我们自己的光阴与伟大电影中的光阴已然流淌在一起了。
然而,现实情形却是大多数不雅观众被一些“半吊子”的见地误导,将这些精品与沉闷或无聊等同起来。罗杰在世时每年都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在各种电影讲习班几次再三破除这种糟糕的见地。他通过“拉电影”,让在场的大多数人理解并爱上了真正电影的“伟大”。
例如2004年的时候,在场的不雅观众都嚷嚷着要看《杀去世比尔》,但罗杰放映的却是法国电影大师雷·诺阿的《游戏规则》——奇迹涌现了,这部1939年的影片所展示的场面调度、人物、镜头、演员错综繁芜的运动,征服了现场的不雅观众,他们久久地谈论,回到宾馆安歇后依然如此。
还有一次是放映小津安二郎的《浮草》。西方人(实在也包括我们)总是先入为主地用禅宗哲学等博识莫测的思维去看待小津,因此会以为他很艰涩。而通过罗杰的放映,不雅观众创造,小津最迷人的地方是处理情绪和素材的适可而止——没有什么博识莫测的东西,他们都被这部美妙的影片俘获了。
当然这并不虞味着罗杰对电影的思想性视而不见。只不过他认为人们基于不同的情由去看电影,而电影的伟大当然是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之中的——他比学术期刊里的影评家更为广博,更有弹性,除了他的片单是“为所有人”之外,他总是一两句话就道破大师的真谛,而其他评论家要写上万字的论文。
例如他说布列松:布列松是电影领域的一位贤人,而《驴子特巴萨》是他最令民气碎的一次祷告;在比较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塔尔科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时,他说,库布里克的影片向外部进发,描述了人类进入宇宙的下一步探索,而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却是向内发掘的,对人类性情的实质和现实发问。塔尔科夫斯基是属于崇奉的。
电影伟大+生命如戏
实际上,人们对影评家的偏见一点都不比对电影的偏见少。在各种写作中,电影评论总是居于鄙视链的底端,乃至网络上不乏“写影评门槛低”“阿狗阿猫都能写影评”这种论调——因此学术期刊的电影论文越写越“博识”。但实际上,通过阅读罗杰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写作的深入浅出是个多么美好而友善的事情,但又有多么高的哀求。
实际上,《伟大的电影》(1)的中文版问世已经十年,重印多次,但是我刚刚知道,《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家认为个中列入的雅克·塔蒂的《于洛师长西席的假期》“不配列入伟大的电影之列”。这当然是缺点得令人发指的见地,同时也能看出美国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构造,它并非总是值得尊重或讴歌。而罗杰的确比他们懂得多。
罗杰的诙谐是骨子里的。在他得知自己罹患家族遗传的癌症后说,这是父母爱孩子的一种表现。记录片《生命如戏》(Life itself)讲述了关于罗杰的影评人生涯,关于他抗癌、直到去世的故事。这个始终洋溢着乐不雅观的讲述没有任何煽情,却依然是催泪的,它见告你,生活、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或许生活正如罗杰对《我的舅舅》的评论:
“我弟弟须要的是一个目标。”阿佩尔夫人流传宣传,而那正好是于洛最不须要的。他只想独自一人,闲逛,欣赏,不赶往任何目的地,或许也无处可去。
让·吕克·戈达尔曾说,“电影不是站台,它是一列火车。”我从前一贯读不懂这句话,直到于洛师长西席对我揭示了它的含义。旅途充满了快乐,而悲哀埋伏在终点。(黑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