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染微恙。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意想不到地招惹了点小毛病。恰如最近的情形:刚做完手头的一个市级课题,厘清了荣氏梅园与20世纪前期无锡工商文化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当代园林中的文化历史地位,校毕全文,上传交稿,当天夜间就喉咙发痒且痛,第二天一早做了个核酸,阴性,那便是普通感冒了。这些天算夜热,紧张写稿十几天,大约是疲倦了吧。既然有恙,就静下心来,歇一歇,随便翻翻闲书,饮点清茶,散散心。
恙,便是病的意思。古人常用此字,抱恙,宿恙,微恙,无恙,分别是说带病、宿病、小病、无病。从前朋友之间通信,常有一句“某某兄,别来无恙”,这是朋友之间的问候语,大致是问候这段韶光身体康健的意思,但如果换成当代汉语,就显得很不文雅了,比如:“某某兄,这段韶光您老兄没发毛病吧?”很粗俗,哪里还有一点朋友之间问候的意思呢?
恙是个形声字,从心,羊声。本义该当与心有关,以是字典阐明其本义为“担忧”,后来才引申而罹病义。如果望字买卖,那便是由于顾虑羊而心忧。羊是最早驯养为家畜的动物之一,自然也是古人主要的财产。如果羊被狼袭杀或被人偷窃,都是主要丢失,故时常担忧之,所谓心坎不安,久而成病。
但古人对恙字另有一种阐明。古人住处草多,有一种毒虫名恙,躲在草丛里,惯于暗中咬人致病。以是,每天醒来,人们相互会问:没被恙咬到吧?汉代应劭的《风尚通》说:“恙,毒虫也,喜伤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劳问,必曰无恙。”听说,恙虫形似臭虫,体红,赤眼,肢四对,全身长细毛,爬动迅速。当代科学研究创造,全天下已知恙虫有3000多种,中国恙虫有记载的约350多种,个中创造叮咬人的至少有12种。大部分恙虫非常小,大小不敷1毫米。恙虫叮咬之后,轻症者皮肤发痒,乃至发炎,重症者会涌现明显的中毒及神经症状等。在这个意义上解读恙字,彷佛可以更加贴切地理解古人授予这个字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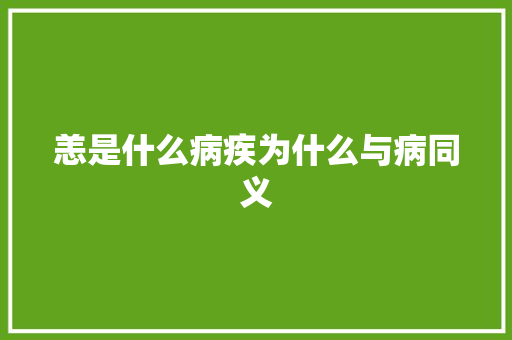
由恙这个字,可以遐想到另一个字:痒。过去一贯以为这个字与羊有关,人靠近羊,会产生一种皮肤觉得,这种觉得被称作“痒”。但如果理解了恙字的本义,我们就能明白,痒这种觉得的来源是由于恙虫,或者其它小虫,恙虫和小虫可能藏在羊身上,并叮咬靠近羊的人,从而导致人产生痒的觉得,而这种痒感是被古人看作毛病的,而且很可能引起内在的毛病。痒,是形声字,疒形,羊声。疒,在当代汉语中被称为病字旁。
恙字是汉字中少见的不带病字旁而指病的字,其他与病干系的汉字,一样平常都是病字旁,如痒,疾,病,痛,痨,疫,瘤,癌等。瘦字也是病字旁,由于在古人看来过于瘦削便是毛病,瘦骨伶仃,形销骨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不是病态便是病相。病字旁写作“疒”,这是一个象形字,最初的字形是一个人靠在床上,靠在床高下不来,当然是由于生病了。以是,当代民间措辞中,常常用病人下不了床作为一种疾病严重的婉转表达。
古人最初用来指人罹病的字,是“疾”,“寡人有疾”这四个字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游说梁惠王行仁政王道,请梁惠王自省一下有什么问题,梁惠王就开门见山,自己有好色的毛病。前几年有部网络小说就名叫《寡人有疾》。针言中有“积劳成疾”、“讳疾忌医”,个中的疾字,都是病的意思。《说文解字》说:疾,病也,从疒,矢声。是把这个字看作形声字的,但反对见地不少,认为这是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疾是表示人的“大”和表示箭的“矢”的组合,而矢射向人的腋下,由此造成人的伤痛。以是,他们认为疾的本义是指人被箭所伤而痛,是会意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里作注说:“矢能伤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会意。”弓箭是古代作战时的利器,可以远间隔伤人,古代医学治疗水平低,为箭所伤之人大都会因箭伤传染而亡。古人为了加大弓箭的杀伤力,还常常在箭头上涂毒,比如吴王阖闾,被越军的染毒飞戈命中脚趾而亡,从受伤至去世亡仅几个小时。在平时生活中,当疾病来时,古人以为就如飞箭一样平常,出乎猜想地就被击中了,于是,疾字从为箭所伤而被引申为病的意思了。到了战国期间,左边的人形的“大”就逐步转化为“疒”,形状犹如一个人靠在床上,表示生病下不了床。疾还有一个意思是迅速,《说文解字》:“速,疾也。”“迅,疾也。”如眼疾手快,奔跑。
当代汉语中疾与病两个字习气地被并用,疾是汉语通用字,病则是汉语一级通用字,疾病,连在一说,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古代,疾与病的意思是稍有差别的。病字涌如今战国,比疾字涌现的晚一些。病的本义是指病情危重,而不是指病本身。《说文解字》认为:“病,疾加也。从疒,丙声。”疾加,便是疾病加重的意思。《论语·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东汉何晏《论语集解》引包贤曰:“疾甚曰病。”意思是疾加重了就叫做病。但有一些学者剖析了《诗经》《山海经》《易经》《尚书》《论语》等八部古代文献中所用病字的各种意思,认为病的本义不是疾病,而是困苦、困厄、重危等,后来被用来形容疾的状态,与疾并用,逐步就引申为与疾同义了。这个字义的转型大致在战国晚期完成,韩非写过一篇《扁鹊见蔡桓公》,先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居旬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居旬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在韩非文中,疾与病基本同义了,但病表示的程度比疾深重了。病字中的丙,并非只是表音,古代以十干配五方,丙为南方之位,南方属朱雀,火性,这个病字可能还意味着染疾者发热发热的状态,这样,疒与丙的组合,就有了会意之义。
瘤是一个与疾病干系的字,历史比较古老,据考在甲骨文中已经有这个字。瘤的本义便是指身体组织上增生的赘物,《说文解字》说:“瘤,肿也。从疒,留声。”在《说文解字》中,瘤写作“癅”,读音与瘤同。《普通文》说:“肉凸曰瘤。”今人一样平常把肿瘤连在一起说,医院里卖力治疗肿瘤的科室叫作肿瘤科。恶性肿瘤被称为癌,癌这个字是在宋代涌现的。当时的年夜夫在治疗病人的实践中,对恶心肿瘤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在1170年景书的《卫济宝书》中,则对这类肿瘤疾病利用了一个新字:癌。疒字旁下面加一个嵒,嵒便是岩,是山上的石头,沉重,坚硬,难以破开,这该当是当时年夜夫对癌的理解。100多年后,有位医学家杨士瀛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对癌的不雅观察:“癌疮如眼,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颈或肩或臂。外症令人晕厥”。癌本来读作岩,这个字1915年才被《中华大字典》和《辞源》收载个中,1961年版《新华字典》首次把癌的读音标识为ai,以避免癌(yan)症的发音与炎症雷同。
以疒作偏旁的字还有不少,如“疫”字,这是个形声字,从疒,役省声,《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字林》说:“疫,病盛行也。”老百姓都罹病了,就像劳役、兵役的军队一样平常被成排成片地盛行传染。以是,古代一样平常把盛行的急性传染病称为“疫”。限于笔墨,其他与“疒”干系的字,就不一一叙说了。
偶有微恙,会略微给人带来一些不舒畅,但也无碍,可以让人从繁杂中暂时脱出身来,修身养神,犹如汽车利用一段韶光之后的保养。而那些长期的、沉重的疾病,就会给人带来许多痛楚,但我记得,在文学艺术史上,却有很多名人名作是与疾病分不开的。比如中国唐代墨客李贺,由于身染疾病,27岁就去世了。他的诗作奇特、怪诞、诡异,感伤而消沉,显然与他的疾病脱不了干系,是天才与病态的结合。美国墨客爱伦•坡患有严重的双相忧郁症,文艺评家认为,他的许多精品都来与内心的烦闷与狂躁。诺贝尔文学奖得到者海明威的作品中常常涌现一个被战役撕裂的残酷天下,他末了自尽了,去世于癌症和烦闷症的双重折磨。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用作品刻画人物的生理和情绪天下的时候,始终伴随着严重的烦闷症,她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她本人被誉为20世纪当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先锋作家。伍尔芙末了投水自尽,留给丈夫的纸条上说,自己已经无法忍受发疯的觉得。虽然生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认为疾病是不少作家和精品的温床,但个中的痛楚不言而喻。以是,还是诚挚地祝愿这个天下和众平生安无事。